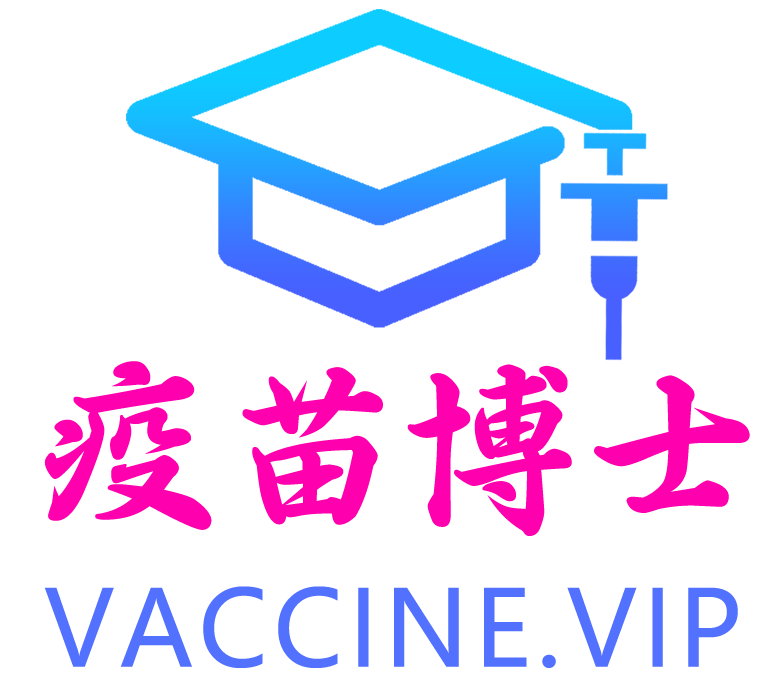What’s Old is New Again: Pertussis
尽管疫苗可用,百日咳是一种特别难以控制的疾病。分子诊断的改进、疫苗成分的变化以及疫苗接种机会的错失导致百日咳发病率的上升。小婴儿面临严重并发症和死亡的最高风险,但孕妇在怀孕期间接种疫苗可以提供保护。婴儿百日咳的表现与成人所见的典型卡他性、阵发性和恢复期有所不同。通过了解所有年龄组的百日咳临床表现,医务人员可以更快地开具适当的抗生素治疗和接触后预防。医务人员也是孕妇和家庭接受基于证据的疫苗接种咨询的重要来源,了解这种疾病的并发症是这些有时困难但至关重要的对话的重要部分。 引言
“没有什么比看着一名患有百日咳的婴儿挣扎着呼吸,而你却无能为力去帮助他们更令人沮丧的了。”——凯瑟琳·爱德华兹 美国的疫苗接种覆盖率正在下降,全球范围内也是如此,导致几种可通过疫苗预防的疾病重新出现。百日咳(百日咳杆菌引起)是这些疾病中最难控制的之一。医疗保健提供者(HCPs)今天比近期更有可能遇到患有百日咳的患者。通过熟悉这种疾病,HCPs可以更好地准备照顾感染患者,并有效地向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关于母婴和儿童疫苗接种重要性的咨询。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
博德特菌是革兰氏阴性、棒状弯曲的微生物;四种物种(百日咳博德特菌、副百日咳博德特菌、支气管败血波德特菌和霍姆斯博德特菌)可引起人类呼吸道疾病。只有百日咳博德特菌产生百日咳毒素(PT),该毒素可灭活G蛋白,并通过降低粘附分子的表达、抑制从血管中渗出和促进从脾等滞留组织的外流来驱动严重的淋巴细胞增多。这些淋巴细胞随后可聚集,导致肺动脉高压和死亡。博德特菌物种还产生其他允许粘附到呼吸上皮细胞的毒力因子,包括丝状血凝素(FHA)、百日咳粘附素(PRN)和菌毛(FIM)。FHA还促进红细胞凝集,而PRN保护细菌免受中性粒细胞的清除。 无论是既往患过百日咳,还是接种过百日咳疫苗,都无法提供完全或终身的免疫力,目前也尚无经证实的保护性实验室关联指标。母体免疫接种能在婴儿接受基础免疫前为其提供保护,这一成功案例明确表明抗体可预防百日咳。不过,近期研究也证实了细胞免疫应答在疾病预防中的重要性 [20-23]。
百日咳自然感染以及全细胞百日咳(wP)疫苗(含完整、灭活且脱毒的百日咳鲍特菌细胞)可刺激产生 Th1/Th17 型 CD4+T 淋巴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应答。与之相反,无细胞百日咳(aP)疫苗则会诱导产生以 Th2 型免疫应答为主的反应 [20-23]。此外,与全细胞百日咳疫苗相比,无细胞百日咳疫苗所含抗原种类更少,因此其诱导的免疫应答范围也更有限。同时,与全细胞疫苗制剂相比,无细胞百日咳疫苗诱导的免疫力衰减速度更快 [24]。
美国已获批并分别推荐给儿童、青少年及成人使用的白喉 – 破伤风 – 无细胞百日咳联合疫苗(儿童剂型:DTaP;青少年 / 成人剂型:Tdap),其成分包含不同剂量的百日咳毒素(PT)、丝状血凝素(FHA)和百日咳杆菌黏附素(PRN);部分疫苗还含有菌毛(FIM)。
完成 DTaP 基础免疫系列接种后,该疫苗的即时保护效力介于 75% 至 90% 之间 [25,26]。而在加利福尼亚州爆发百日咳疫情期间,模型研究显示,接种 Tdap 疫苗后 4 年,其保护效力会降至约 9%[27]。
早在 16 世纪,人类就已发现百日咳。世界各地的社群均根据其独特的咳嗽症状为这种疾病命名:意大利语中称其为 “tosse canina”,意为 “犬吠样咳嗽”;法语中称为 “coqueluche”,意为 “鸡鸣样咳嗽”;而中文里的 “百日咳”,则对应 “持续百天的咳嗽” 这一含义 [17]。
在美国,百日咳的公共卫生负担与百日咳疫苗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20 世纪 40 年代末,全细胞百日咳(wP)疫苗与白喉、破伤风类毒素联合制成的 “白喉 – 破伤风 – 全细胞百日咳联合疫苗(DTwP)” 获批前,美国每年的百日咳病例数在 10 万至 20 万之间。在推行 “5 剂次 DTwP 疫苗接种系列” 后,百日咳的年发病率大幅下降,1976 年降至最低点,仅报告 1010 例 [17,28]。
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由于公众担忧疫苗的反应原性(即接种后引发不良反应的可能性),且出现关于接种后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的传言,疫苗接种率下降,百日咳病例数随之回升 [28,29]。此外,两起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疫苗的疑虑:一是日本两名婴儿接种 DTwP 疫苗后死亡(尽管未证实二者存在因果关系);二是瑞典使用的某款 DTwP 疫苗被发现无效;同时,英国还出现了关于疫苗相关脑病的担忧。这些事件导致多个国家全面停止或大幅减少 DTwP 疫苗接种,随后百日咳疫情爆发,造成大量婴儿死亡 [30-34]。
针对 DTwP 疫苗反应原性的担忧,推动科研人员开展深入研究,旨在研发反应原性更低的疫苗。研究核心思路是分离百日咳鲍特菌的免疫原性成分,并将这些成分用作疫苗抗原 —— 这一研究最终促成了无细胞百日咳(aP)疫苗的诞生。此后,aP 疫苗与白喉、破伤风成分联合,形成 “白喉 – 破伤风 – 无细胞百日咳联合疫苗(DTaP)”,并于 20 世纪 90 年代获批。
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开展的多项研究(针对不同配方的 DTaP 疫苗)显示 [25,35-39]:在预防婴儿实验室确诊百日咳方面,DTaP 疫苗的反应原性低于 DTwP 疫苗,且保护效力与 DTwP 疫苗相当。基于这些数据,美国于 1992 年将 DTaP 疫苗纳入儿童免疫接种系列,用于第 4 剂和第 5 剂接种;1997 年起,整个儿童免疫接种系列均改用 DTaP 疫苗 [17]。
在之后的几年里,百日咳得到了良好控制,但 21 世纪初爆发的多起百日咳疫情表明,DTaP 疫苗诱导的免疫力会随时间推移而衰减 [28,40,41]。为此,科研人员研发了加强针疫苗(Tdap)—— 其抗原成分与 DTaP 疫苗相同,但部分成分的剂量有所降低 [42]。2005 年,美国将 Tdap 加强针纳入儿童免疫接种程序,推荐 11-12 岁青少年接种,并将其纳入现行学校入学疫苗接种要求 [43,44]。
新冠疫情期间推行的社交距离措施,使百日咳病例数显著下降;但随着防疫措施放宽,病例数激增,超过了疫情前水平。2024 年,美国报告的百日咳病例达 35435 例,其中包括 6 例婴儿死亡(见图 1)。发病率最高的三个州分别是阿拉斯加州、爱达荷州和威斯康星州,发病率依次为每 10 万人 81 例、54 例和 45 例 [45]。
最新报告数据显示,近半数已报告病例发生在 11-19 岁人群中,17% 发生在 20 岁以上人群;但需注意的是,老年患者的百日咳病例很可能存在漏诊情况 [45]。有研究估计,在青少年和成人中,每出现 1 例临床确诊的百日咳病例,就伴随有 5 例无症状感染 —— 这一情况无疑会加剧百日咳在社区中的传播 [46]。
疫情后,全球百日咳发病率均有所上升,多个大洲均报告了疫情爆发 [47]。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新冠疫情前的百日咳常规监测数据可能并不完整 [48,49],但广泛接种疫苗已显著降低了这些国家的百日咳病例数和死亡率 [50]。放眼全球,各国在百日咳疫苗接种可及性、检测可及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同时,由于医务人员对百日咳典型及非典型临床表现的认知不足,漏诊情况普遍存在;此外,不同国家的病例报告详尽程度也各不相同 [51,52]。
在年长儿童和成人中,百日咳的临床表现通常分为 3 期:
- 卡他期:以咳嗽和流涕为主要症状,通常与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URTI)难以区分,且常无发热症状。此阶段咳嗽会持续加重 1-2 周,之后患者进入痉挛期。
- 痉挛期:持续数周,患者会出现阵发性剧烈咳嗽,每次咳嗽后会伴随 “鸡鸣样” 吸气声(因声门部分阻塞,吸气时气流快速通过狭窄通道产生)。患者常出现咳嗽后呕吐,长期可能导致体重下降 [17,52,53]。
- 恢复期:咳嗽发作的严重程度和频率逐渐降低,但咳嗽症状可能持续数月;即使患者看似已完全康复,在病毒感染后咳嗽也可能复发 [13,54]。
百日咳的疾病谱较广,无症状感染和轻症感染较为常见,在青少年和成人中尤为突出 [55-58]。需注意的是,副百日咳鲍特菌感染的临床表现与百日咳相似,但通常病程更短、症状更轻 [9]。
婴儿感染百日咳后病情通常更严重,且并发症风险更高。疾病初期,婴儿可能看似状态尚可,症状与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相似;典型的痉挛性咳嗽和 “鸡鸣样” 吸气声可能不出现,但呼吸暂停较为常见 [17,53]。婴儿的白细胞计数可高达 100,000 个 / 立方毫米,且淋巴细胞增多的程度与不良预后相关 [13,14,17,53,59]。因此,婴儿若出现明显淋巴细胞增多,需高度怀疑百日咳。
百日咳最敏感且快速的检测方法是聚合酶链反应(PCR),可作为单独检测项目,也可纳入呼吸道病原体多重检测 panel 中。咳嗽发作后的前 3-4 周内,PCR 检测结果通常为阳性,但若超过 4 周,检测敏感性会下降 [60,61]。
从历史角度看,在咳嗽发作的前 2 周内,细菌培养曾被视为百日咳诊断的 “金标准”—— 其特异性高,且对流行病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60,62]。然而,细菌培养存在明显局限性:检测服务不易获取、从样本采集到出结果的周转时间长,且检测敏感性不稳定(尤其在疾病后期),因此难以作为常规诊断手段 [60,63,64]。
血清百日咳毒素(PT)抗体滴度升高,对疾病后期的百日咳诊断有辅助意义,尤其适用于临床表现不典型的青少年和成人 [60]。尽管目前尚未明确统一的诊断临界值,但对于近期未接种过百日咳疫苗、且符合特定临床和流行病学特征的患者,若其抗 PT 免疫球蛋白 G(IgG)滴度≥100 IU/mL(采用经标准参考血清校准的检测方法),则高度提示近期感染百日咳 [65]。不过,临床医生需注意:市售检测试剂盒的性能差异较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选择分子诊断方法(如 PCR)[60,66]。
在年长儿童和成人中,百日咳引发严重并发症的情况较少见,但可能出现呕吐、尿失禁等令人不适的症状 [17,53]。少数患者可能发生继发性细菌性肺炎、中耳炎、晕厥、肋骨骨折等并发症 [52,67-69],另有报道称部分患者可能出现气胸、颈动脉夹层、癫痫发作及脑病 [52,68-73]。无论病情轻重,百日咳都会带来显著的经济负担,包括因患病导致的缺课、缺勤等 [74]。
婴儿发生百日咳严重并发症的概率远高于年长人群:在美国,大多数 2 月龄以下的百日咳患儿需住院治疗 [75]。约 2/3 的婴儿患者会因咳嗽引发喉痉挛或迷走神经刺激,进而出现呼吸暂停 [17,76];严重肺动脉高压也是婴儿百日咳的致命性并发症之一,其发病机制被认为与严重淋巴细胞增多导致的肺血管阻塞及呼吸道黏膜脱落有关 [59,77]。此外,婴儿还可能因呼吸暂停发作时的缺氧,或因抗利尿激素分泌异常综合征引发的低钠血症,出现癫痫发作 [71,78-80]。
百日咳相关死亡病例(包括美国近期报告的病例 [81])几乎均发生在 3 月龄以下婴儿中;此外,百日咳还与 “婴儿突发性不明原因死亡” 事件存在关联 [82,83]。近期研究显示,美国百日咳的病死率超过 1%[14]。
对于所有确诊或疑似百日咳的患者,建议尽快启动抗生素治疗。若在疾病早期(痉挛期发作前)用药,可能缓解症状;即便在疾病后期用药,虽难以影响病程进展,但可降低疾病传播风险。
大环内酯类药物(如阿奇霉素)是百日咳的一线治疗药物;对于 2 月龄以上、无法使用阿奇霉素的患者,可选用复方磺胺甲噁唑作为替代药物。尽管有研究表明阿奇霉素可能与极年幼婴儿的幽门狭窄相关,但考虑到该人群中百日咳常引发严重并发症,临床认为用药获益远大于风险 [17,65,84]。
除抗生素治疗外,百日咳的管理以支持治疗为主,具体措施需结合患者年龄和病情严重程度调整:
- 对于婴儿患者,若出现肺动脉高压、心源性休克或严重淋巴细胞增多,可考虑进行换血治疗;且在多器官功能障碍发生前实施该操作,效果更佳 [14,17,53,85-88]。
- 对于接受机械通气仍持续恶化的年幼婴儿,可考虑采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治疗;但需注意,回顾性数据显示,需接受此类高级生命支持的婴儿病死率较高 [14,87]。
- 不推荐使用糖皮质激素:回顾性研究及动物模型均表明,使用糖皮质激素会增加患者死亡风险 [14,86,89]。
- 一氧化氮虽可用于治疗其他类型的肺动脉高压,但对于重症百日咳婴儿,尚无证据显示其能改善预后 [86,87]。
- 有病例系列研究提及使用羟基脲治疗,但目前尚无确凿的临床试验证据支持该疗法的有效性 [90,91]。
百日咳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患者在卡他期及痉挛期初期传染性最强,且婴幼儿的细菌排出时间通常长于年长儿童。既往感染史、疫苗接种史及抗生素治疗均可缩短患者的传染期。
百日咳感染控制的具体措施包括:
- 住院患者管理:需对住院患者采取飞沫隔离措施。
- 门诊患者管理:接受有效治疗的门诊患者,需在用药 5 天后才可返回工作单位、学校或托育机构;未接受治疗的患者则需隔离 21 天 [65,92]。
- 暴露后预防(PEP):
- 应向患者的家庭成员及其他密切接触者(如同一托育机构的人员)提供暴露后预防。
- 不常规推荐对学校内所有接触者进行暴露后预防,但对于存在严重百日咳发病风险的接触者,或需接触年幼婴儿及其他高风险人群的接触者,应考虑实施暴露后预防。
- 在医疗保健机构中,若暴露后的医护人员(HCP)需接触新生儿、孕妇等高危患者,则应接受暴露后预防。
- 目前医疗保健机构中,“暴露” 的接触时长和接触类型尚未有明确界定,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认为,近距离无防护面对面接触(如体格检查时的接触)属于职业暴露 [93,94]。
- 暴露后预防的用药方案与百日咳治疗方案相同(见表 1)。
- 即便接触者有疫苗接种史,仍需接受暴露后预防;若接触者疫苗接种不完整,除抗生素预防外,还需补种含百日咳成分的疫苗 [65,95]。
美国 CDC 目前推荐的百日咳疫苗接种方案如下:
- 基础免疫(儿童期):推荐在 2 月龄、4 月龄、6 月龄、15-18 月龄及 4-6 岁时接种白喉 – 破伤风 – 无细胞百日咳联合疫苗(DTaP)[96,97]。
- 加强免疫(青少年及成人期):
- 推荐 11-12 岁青少年接种 1 剂白喉 – 破伤风 – 无细胞百日咳联合疫苗(Tdap)作为加强针,若未及时接种,可补种至 18 岁。
- 19 岁及以上、从未接种过 Tdap 的人群,需接种 1 剂 Tdap。
- 疫苗接种灵活性调整(2019 年起):
- 每 10 年需接种 1 剂白喉 – 破伤风联合疫苗(Td)的人群,可灵活选择接种 Tdap。
- 曾接种过 Tdap、因伤口需预防破伤风的人群,可灵活调整接种方案。
- 7 岁及以上、百日咳疫苗接种史不完整的人群,在补种程序中可灵活安排多剂接种 [104]。
- 不良反应:与含全细胞百日咳成分的疫苗(如 DTwP)相比,含无细胞百日咳成分的疫苗(如 DTaP、Tdap)引发局部和全身不良反应的概率显著更低,但仍可能出现局部反应(如红肿)和发热 [98]。约 2% 的儿童在接种第 4 剂或第 5 剂 DTaP 后,可能出现接种侧大腿或上臂全肢肿胀,临床医生若不熟悉该现象,可能将其误诊为蜂窝织炎或肌炎;此类患者无需因此停用后续剂次的疫苗 [65]。
- 安全性证据:目前无证据表明接种 DTaP 会增加癫痫发作风险,且该疫苗引发低张力 – 低反应性发作的情况极为罕见 [100-103]。
- 禁忌证:DTaP 和 Tdap 疫苗的唯一禁忌证包括:① 对既往接种的同类疫苗或疫苗成分存在严重过敏反应(如过敏性休克);② 既往接种 DTwP、DTaP 或 Tdap 后 7 天内发生原因不明的脑病 [97]。
由于含百日咳成分疫苗的保护期有限、其流行病学影响尚不明确且存在成本考量,目前尚未明确推荐为普通公众或非孕期医护人员常规重复接种 Tdap [104,105]。
表 1 推荐的百日咳暴露后预防与治疗方案
抗生素类别 | 年龄组 |
| | <1 月龄 | 1-5 月龄 | ≥6 月龄 |
| 首选药物 |
| 阿奇霉素(Azithromycin) | 每日 10mg/kg,每日 1 次,连用 5 天 | 每日 10mg/kg,每日 1 次,连用 5 天 | 第 1 天:10mg/kg(最大剂量 500mg),每日 1 次;第 2-5 天:5mg/kg(最大剂量 250mg),每日 1 次 |
| 克拉霉素(Clarithromycin) | 不推荐 | 每日 15mg/kg,分 2 次服用,连用 7 天 | 每日 15mg/kg(最大剂量 1g / 天),分 2 次服用,连用 7 天 |
| 红霉素(Erythromycin) | 不推荐 | 每日 40-50mg/kg,分 4 次服用,连用 14 天 | 每日 40-50mg/kg(最大剂量 2g / 天),分 4 次服用,连用 14 天 |
| 替代药物 |
| 复方磺胺甲噁唑(TMP-SMX) | 禁用 | <2 月龄者禁用;≥2 月龄者:甲氧苄啶(TMP)每日 8mg/kg + 磺胺甲噁唑(SMX)每日 40mg/kg,分 2 次服用,连用 14 天 | 甲氧苄啶(TMP)每日 8mg/kg + 磺胺甲噁唑(SMX)每日 40mg/kg(最大剂量:TMP 320mg / 天),分 2 次服用,连用 14 天 |
为孕期人群接种疫苗可预防婴幼儿百日咳及其相关死亡和发病。该策略能提高母体百日咳抗体水平 —— 孕晚期母体抗体通过胎盘的传递效率最高,可为婴儿提供保护,直至其开始接种基础免疫疫苗。
这一策略的首批 “概念验证” 研究可追溯至 20 世纪 30-40 年代:当时有少量孕妇在孕晚期接种了全细胞百日咳(wP)疫苗 [106,107]。研究发现该接种方式安全性良好,且接种疫苗的母亲所生婴儿未感染百日咳。21 世纪初,这一接种方案再次被提出:当时有报告显示,因年龄过小尚未开始基础免疫接种的婴儿百日咳死亡病例数不断增加;同时,“茧式保护” 策略(通过为产后母亲及婴儿照护者接种 Tdap 疫苗,为婴儿提供间接保护)被证实成本高昂、实施难度大,且未能显著降低婴儿百日咳发病率 [97,108,109]。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美国 CDC 于 2012 年推荐所有孕妇在每次孕期均接种 Tdap 疫苗,最佳接种时间为孕 27-36 周 [59]。推荐 “每次孕期均接种” 的依据是:观察发现 Tdap 疫苗诱导产生的百日咳抗体衰减速度较快,首次孕期接种产生的抗体无法为后续孕期出生的婴儿提供保护 [97,110]。目前,许多高收入国家已推荐孕期接种该疫苗,但并非所有高收入国家均已采纳 [111]。
针对 “孕期接种疫苗预防极年幼婴儿百日咳” 的效果评估显示:该措施可使婴儿百日咳住院率降低 90% 以上,死亡率降低 95%[75,97,112-116]。但疫苗保护效力会随婴儿年龄增长而下降,婴儿 7-8 月龄时保护效力降至 43%,8 月龄后则完全失去保护作用 [117]。
母亲孕期接种 Tdap 疫苗后,其婴儿在接种基础免疫疫苗时产生的免疫应答会减弱,但在后续剂次疫苗接种中,婴儿的免疫应答会恢复正常,且百日咳发病率并未升高 [118,119]。从妊娠结局和婴儿健康状况来看,孕期接种 Tdap 疫苗是安全的 [113,118,120-123]。
目前仍需持续监测和评估这一预防策略的效果,尤其是针对母亲仅接种过含无细胞百日咳成分(aP)疫苗的婴儿 —— 部分研究表明,与接种过全细胞百日咳(wP)疫苗的父母相比,仅接种过 aP 疫苗的父母对 Tdap 疫苗的抗体应答略低 [123]。尽管如此,孕期接种疫苗仍是预防极年幼婴儿百日咳相关发病和死亡的最佳策略。
理想的百日咳疫苗应具备以下特点:预防感染和疾病的临床效力高、能阻断百日咳鲍特菌传播、保护期长、安全性有保障。由于现有疫苗尚未完全满足这些要求,目前已有多种新型疫苗研发方案正在推进,具体包括:
减毒活疫苗(如 ILiAD 生物技术公司研发的减毒活 BPZE1 疫苗):该疫苗通过敲除百日咳鲍特菌的多个毒力基因制成,采用鼻内接种方式,旨在同时诱导黏膜免疫和全身免疫。研究已证实其在人体中安全性良好且具有免疫原性,可诱导产生体液抗体和黏膜抗体 [124-126]。针对青少年和成人的该疫苗 III 期临床试验即将启动。
基因灭活百日咳毒素(PT)疫苗:与传统化学灭活 PT 疫苗不同,该疫苗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实现 PT 灭活,可诱导更强的 PT 免疫应答,目前正处于评估阶段 [127,128]。
其他改良疫苗:目前还在开展多项研究,包括在现有百日咳疫苗中添加多种外膜蛋白、其他百日咳抗原、佐剂及免疫刺激剂等;同时,百日咳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的动物实验也在进行中 [129-133]。
疫苗接种仍是控制百日咳地方性流行和暴发的最有效手段。但在美国,百日咳疫苗覆盖率仍存在显著缺口。CDC 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尽管有学校入学疫苗接种要求,且疫苗的医学禁忌证极少,但 2024-2025 学年美国幼儿园儿童的 DTaP 疫苗接种率仅为 92.1%。各州接种率差异极大,爱达荷州最低(78.3%),康涅狄格州和弗吉尼亚州最高(98.2%)[134]。
疫苗接种不完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因素包括:越来越多的州允许基于宗教或哲学信仰豁免疫苗接种;公众对疫苗的普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源于对疫苗风险与获益的虚假信息误导,且新冠疫苗相关虚假信息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134-136]。
美国儿科学会(AAP)已提出基于证据的策略,帮助医护人员(HCP)与对疫苗价值存疑的父母沟通 [137]。这些策略强调 “积极倾听”,并认可父母经常接触不实疫苗信息的现实。沟通中的核心信息之一是:父母与医护人员目标一致,均致力于为孩子采取正确的健康措施。此外,还需注意:绝大多数父母都会为孩子接种百日咳疫苗,医护人员应避免将 “不接种疫苗” 的选择正常化 [138]。
预防百日咳相关死亡的主要手段是孕期疫苗接种。尽管有充分证据表明孕期接种 Tdap 疫苗安全且效果显著,但美国孕期 Tdap 疫苗接种率仅约 50%[75,97,112-115,118,120-122]。
新冠疫情后,尽管部分孕妇对接种 Tdap 疫苗的犹豫情绪有所上升 [139],但孕期 Tdap 疫苗接种率仍高于疫情前基线水平 [140]。研究表明,与儿童疫苗接种类似,孕妇接受疫苗接种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医护人员的明确推荐 [141-143]。
针对 Tdap 疫苗的研究显示:若医护人员明确推荐接种,且提供现场接种服务或转诊至接种点,孕期 Tdap 疫苗接种率可达 71%;反之,若医护人员未作出推荐,孕期 Tdap 疫苗接种率仅为 1%[115,143]。
最后需强调:当临床医生能告知患者 “自己及家人、同事均已接种疫苗” 时,其提出的疫苗接种建议会更具说服力。因此,需正视并改善医护人员单剂 Tdap 疫苗接种率不足的现状 [97]。
百日咳仍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健康威胁:对年长青少年和成人而言,它至少是一种不便且干扰正常生活的疾病;对婴幼儿而言,它则是导致发病和死亡的重要原因。医护人员通过熟悉百日咳相关知识,可成为防控该疾病的重要防线 —— 具体措施包括早期识别病例、采取规范的感染控制措施,而最重要的或许是推广疫苗接种,将其作为控制这一复燃疾病的最佳手段。
缩写词
参考文献
Naureckas Li C, Edwards KM, Kaplan SL, Marshall GS, Parker S, Healy CM. What’s Old Is New Again: Pertussis. Pediatrics. 2025 Nov 1;156(5):e2025072868. doi: 10.1542/peds.2025-072868. PMID: 41038623.Hits: 51